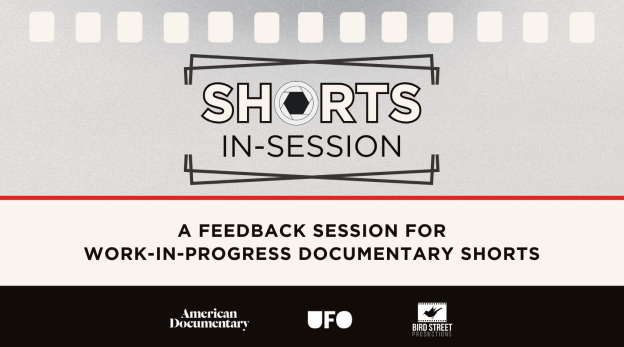奧斯卡獎,俗稱「小金人獎」,被廣泛認為是「演員職業生涯的巔峰」及「全球電影業最負盛名的獎項」。獲得那座令人垂涎的金色小雕像,往往被視為「電影業的終極認可」,是同行們對演員的奉獻精神與藝術造詣達到「如此具影響力,足以讓他們將您推舉為該類別最佳者」的深刻肯定。這份獨特的榮譽,象徵著少數人才能達到的表演境界。
儘管享有如此崇高的聲望,令人驚訝的是,許多好萊塢備受敬重的才華之士,這些年復一年持續繳出「模範佳作」的演員們,卻發現自己一再與競爭激烈的奧斯卡表演獎項「擦肩而過」。這種一再發生的現象,常被影迷與評論家視為一種「藝術與品味的罪行」。
本文旨在表彰十位此類傑出影人的職業生涯,肯定他們對電影藝術的巨大貢獻。正如《娛樂周刊》所恰當指出的,「未獲獎並不會使演員的才華變得平庸。事實上,我們敢說,一些未獲奧斯卡獎的明星,將比某些確實贏得金像獎的人更能經得起時間的考驗。」他們的故事不僅彰顯了個人的才華,也揭示了奧斯卡投票過程中錯綜複雜、時而令人費解的動態,以及電影成就的多面性。
這些演員們數十年來屢獲學院提名,這本身就突顯了他們非凡的才華。這種持續的肯定,與未能獲獎的結果並列,使得他們的奧斯卡之路尤其引人注目且值得探討。
無冕的才子佳人

1. 葛倫克蘿絲:奧斯卡「近在咫尺」的紀錄保持女王
葛倫克蘿絲是舞台與大銀幕的巨擘。她輝煌的職業生涯橫跨五十餘載,榮獲無數獎項,包括三座黃金時段艾美獎、三座東尼獎以及三座金球獎。2019年,《時代》雜誌將她評為全球百大最具影響力人物之一,足證其深遠的影響力。克蘿絲以其卓越的 versatility(多樣性)及深刻詮釋「複雜且引人入勝角色,兼具深度、張力與脆弱性」的能力而備受讚譽。她是一位能持續「為每個角色注入生命力」的演員,巧妙地「同等程度地展現脆弱與力量」。除了在表演藝術上的巨大貢獻,克蘿絲也是心理健康意識和女權的熱心倡導者。
她的奧斯卡之路堪稱傳奇:克蘿絲保持著在世演員中,入圍最多次卻未獲得任何一座奧斯卡最佳演員獎的紀錄,與已故的彼得奧圖並列,兩人皆累積八次表演獎項提名卻未能抱回小金人。這一連串非凡的提名本身就充分說明了學院對她在各種角色和電影時代中卓越才華的持續認可。她的提名包括:以《蓋普眼中的世界》(1982)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女權母親角色入圍最佳女配角;《大寒》(1983)中詮釋嬰兒潮世代的典型人物;《天生好手》(1984)中飾演動人的愛人角色;以及多年後以《絕望者之歌》(2020)入圍。她的最佳女主角提名則來自她最具代表性的一些角色:《致命的吸引力》(1987)中危險痴迷的艾лек絲佛瑞斯特;《危險關係》(1988)中狡猾且善於操控的梅黛夫人;《變裝男侍》(2011)中她轉型飾演一位以英國男管家身份生活的女性;以及她在《愛・欺》(2018)中備受好評的演出。
在這些作品中,有幾部演出讓她一度看似與奧斯卡小金人近在咫尺。她在《致命的吸引力》中對艾лек絲佛瑞斯特的詮釋成為文化試金石,將她推向國際巨星的地位,並讓「兔子殺手」(bunny boiler)一詞深植人心。羅傑伊伯特讚揚她的表演「駭人卻又始終合情合理」,並指出詹姆斯迪爾登的劇本讓她得以「用甜言蜜語作餌,再以嫉妒、佔有慾,最終以罪惡感設下圈套」。僅一年後,她在《危險關係》中飾演的馬基維利式梅黛夫人為她贏得另一次最佳女主角提名與熱烈好評。許多影評人與影迷至今仍認為,她當年憑此角色的演出絕對值得一座奧斯卡獎。伊伯特讚揚她與約翰馬可維奇在銀幕上對手戲的「完美」,他們「機鋒相對的對話轉化為令人疲憊的言語遊戲,靈魂的網球賽」。數十年後,她在《愛・欺》(2018)中飾演瓊安卡索曼——一位面對為其名譽卓著的丈夫所做出一生妥協的女性——為她帶來第七次最佳女主角提名,以及金球獎、美國演員工會獎和影評人票選獎等一系列重要獎項。她的表演被譽為「令人驚艷」、「沉靜而複雜,細膩入微且充滿情感」,導演比昂魯格更經常將鏡頭聚焦於她充滿力量的無言反應。對許多人而言,這似乎是她終結奧斯卡獎荒的時刻,豈料奧莉薇雅柯爾曼以《真寵》爆冷勝出。
克蘿絲屢次與奧斯卡失之交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她總是面臨極其強勁的對手,敗給了當年演出經典或生涯代表作的女演員,例如《窈窕淑男》的潔西卡蘭芝、《月色撩人》的雪兒、《控訴》的茱蒂佛斯特以及《鐵娘子》的梅莉史翠普。關於她後期生涯的選片也持續存在爭議,部分評論家認為像《愛・欺》和《絕望者之歌》這類為她贏得提名的電影,或許是「保守的載體」或「安全的奧斯卡誘餌」,未能產生她早期一些更具風險性角色所帶來的廣泛電影影響力。然而,她在《愛・欺》中的演出無疑廣受好評。另一種觀點則認為,雖然她的電影評價很高,但她可能未曾主演過那種「無可否認的影史偉大鉅片」,讓她的落敗感覺像是一次絕對的、顛覆共識的震撼。
儘管未獲奧斯卡最佳演員獎,葛倫克蘿絲作為「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女演員之一」的地位無可爭議。她深遠的影響力建立在她卓越的 versatility(多樣性)、「沉浸式的表演風格」,以及她挖掘「一個角色或單一時刻中驚人層次」的獨特能力之上。電影史學家卡莉畢尚將她與蓓蒂戴維斯和梅莉史翠普等銀幕傳奇人物並列為過去八十年來的頂尖女演員,理由是她「選擇角色的膽識……以及她的毅力」。她憑藉從反派到母親形象、從古裝貴族到現代女性等多元角色獲得八次提名,突顯了學院確實一再認可的非凡穩定性與廣度。弔詭的是,正是這種穩定性可能促成了此一局面;學院一次又一次地肯定她的才華,然而,贏得獎項所需的角色影響力、電影聲望、對手實力以及當時「奧斯卡風向」的特定組合卻與她無緣。她的每次落敗,往往是輸給了正值生涯巔峰時刻,或演出勢不可擋電影的女演員,這突顯了奧斯卡獎的獲得往往不僅僅取決於單一表演的品質;更關乎該表演在特定年份的競爭與文化背景下,以何種非常具體的方式產生共鳴。

2. 艾美亞當斯:六度提名,魅力百變的演技派
艾美亞當斯開創了非凡且多元的演藝生涯,最初以在獨立電影《六月蟲》(2005)和迪士尼歌舞片《曼哈頓奇緣》(2007)中「備受好評地詮釋天真迷人角色」而廣為人知。然而,她令人印象深刻的戲路很快就展露無遺,憑藉在《誘.惑》(2008)、《大師》(2012)、《瞞天大佈局》(2013)和《為副不仁》(2018)中的精湛演出,深入探索複雜的戲劇領域。她的作品集展現了她塑造多樣典型角色的能力,從睜大眼睛的迪士尼公主到「誘人的女騙徒」。
這種 versatility(多樣性)與持續的卓越表現為她帶來了六次奧斯卡獎提名卻無一獲獎的紀錄,此一數據促使《娛樂周刊》將她形容為「此現象的代表人物」。她的提名橫跨女配角與女主角獎項:五次最佳女配角提名來自《六月蟲》(2005)、《誘.惑》(2008)、《燃燒鬥魂》(2010)、《大師》(2012)以及《為副不仁》(2018);一次最佳女主角提名則來自《瞞天大佈局》(2013)。此紀錄使她與銀幕傳奇黛博拉蔻兒和黛瑪烈達並列,成為未獲獎女演員中提名次數第二多者,僅次於葛倫克蘿絲。
亞當斯在《六月蟲》(2005)中飾演活潑多話的艾希莉強斯頓,這個突破性的角色立即宣告了她作為主要才華演員的到來,為她贏得了首次奧斯卡提名和廣泛的影評關注。影評人讚揚她「令人眼睛為之一亮且溫暖人心」的表演,指出她「即使面對悲劇也散發著如此的喜悅」,並巧妙地避免將艾希莉簡化為一個刻板印象。該片本身被譽為「觀察入微的生活片段」。她在《誘.惑》(2008)中飾演天真易受影響的詹姆士修女,為她贏得了第二次提名,評論家讚揚她「甜美天真」的舉止,以及她的眼神如何傳達角色的純真與內心衝突。
為了展現戲路,亞當斯在《燃燒鬥魂》(2010)中反傳統地飾演了強悍、精明世故的夏琳佛萊明,為她贏得了第三次奧斯卡提名。影評人觀察到她為角色帶來了「魅力」,「全情投入於素材之中」,呈現出巧妙平衡「脆弱與堅韌」的表演。羅傑伊伯特讚揚她對一位擁有「堅強意志」女性的「頭腦清晰」的詮釋。她的首次最佳女主角提名來自她在導演大衛歐羅素的《瞞天大佈局》(2013)中飾演的女騙徒辛德妮普羅瑟,這部群戲電影獲得了廣泛好評。亞當斯因其「性感撩人且充滿理智情感的詮釋」,傳達出「機智女商人內心深處的脆弱」而備受讚譽。雖然未獲奧斯卡提名,但她在《異星入境》(2016)中飾演語言學家露易絲班克斯博士一角,卻經常被認為是她的最佳演出之一,也是奧斯卡的一大遺珠。《視與聽》雜誌讚揚她傳達出「天生的智慧,卻不落入書呆子刻板印象的窠臼」,她被廣泛視為「一部看似最佳影片大熱門電影的情感核心」。近期,她在《為副不仁》(2018)中轉型飾演琳恩錢尼,為她帶來另一次最佳女配角提名,影評人注意到她與克里斯汀貝爾之間強烈的化學反應。
亞當斯的奧斯卡之路屢屢敗給強勁的對手,包括瑞秋懷茲(《疑雲殺機》)、潘妮洛普克魯茲(《情遇巴塞隆納》)、她在《燃燒鬥魂》的同片演員瑪莉莎李奧、安海瑟薇(《悲慘世界》)、瑞吉娜金(《藍色比爾街的沉默》)以及凱特布蘭琪(《藍色茉莉》)。《異星入境》的提名遺珠至今仍是個令人費解的討論點,尤其考量到該片獲得了包括最佳影片和最佳導演在內的八項其他提名。這個例子突顯了即使是在一部備受讚譽的電影中擔任主角且廣受好評的演出,也未必能保證獲得表演獎項提名,這指向了奧斯卡獎選擇有時難以預料的本質。
儘管未獲奧斯卡獎,艾美亞當斯被廣泛認為是「我們當代最優秀的在職演員之一」。她的作品集證明了她令人印象深刻的戲路以及在各種不同類型電影中持續繳出令人難忘、備受好評演出的能力。她的提名模式,主要集中在女配角獎項,往往使她置身於強大的群戲陣容中,其出色表現是整體成功的一部分。這可能導致她獲得肯定,但最終未能擊敗那些在當年角色或許更為核心或「更搶眼」的表演者。她唯一一次最佳女主角提名,則面臨了凱特布蘭琪壓倒性的得獎演出。《異星入境》的遺珠進一步複雜化了此一局面,暗示著除了純粹的才華或角色核心性之外的因素,也可能影響提名過程。然而,亞當斯在奧斯卡話題中的持續存在,鞏固了她作為一位才華屢獲同行肯定與讚賞的演員地位。

3. 艾德華諾頓:張力十足的變色龍
艾德華諾頓以其灼熱的張力與對技藝毫不妥協的態度,甫一登上影壇便立即脫穎而出。從他最早期的角色開始,他就展現出偏好具藝術挑戰性的項目,而非純粹的商業製作,這一特點貫穿了他大部分的職業生涯。除了演戲,諾頓也涉足導演與製片,創立了 Class 5 Films。他的表演常帶有「對二元性的迷戀」,並以其令人印象深刻的轉型能力著稱,鮮少重複扮演同類型的角色。
諾頓的影響力是如此直接,以至於他憑藉最初幾個主要角色便獲得了奧斯卡獎提名。他的奧斯卡提名紀錄包括四次:憑藉在《驚悚》(1996)中爆發性的處女作及在《鳥人》(2014)中複雜的角色入圍最佳男配角,並預計將以《A Complete Unknown》(根據2025年初的資訊,預計於2025年頒獎典禮提名)。他唯一一次最佳男主角提名則來自他在《美國X檔案》(1998)中令人難忘的演出。
諾頓在電影處女作《驚悚》中飾演艾倫史丹佛,一位看似無辜,被控犯下殘酷謀殺罪的祭壇男童,其演出可謂石破天驚。這個角色以驚人的性格轉變著稱,為他贏得了立即的影評讚譽、一座金球獎以及他的首次奧斯卡提名。羅傑伊伯特讚揚諾頓「完全令人信服」的詮釋,巧妙地玩弄了角色隱藏的深度。這次的處女秀如此強大,以至於「奠定了他的整個職業生涯基礎」。隨後,他又在《美國X檔案》中帶來另一場精湛演出,憑藉其對德瑞克溫亞的令人不安且強而有力的刻劃獲得最佳男主角提名。德瑞克是一位魅力十足的新納粹領袖,經歷了痛苦的轉變。《帝國》雜誌稱讚其為「一場樹立艾德華諾頓為同代最具潛力性格演員的傑出表演」,讚揚他即使在如此猙獰的角色中仍能保留「一絲人性」。據報導,諾頓深度參與了該片最終剪輯版本的塑造,這一點雖引發些許爭議,但也顯示了他對作品的投入。多年後,他憑藉《鳥人》獲得第三次奧斯卡提名,片中他飾演麥可夏納,一位才華洋溢但性格不羈的百老匯方法派演員,其傲慢與米高基頓的角色產生衝突,象徵著好萊塢名流與戲劇藝術完整性之間的張力。
儘管這些演出備受讚譽並獲得提名,諾頓至今仍未抱回奧斯卡獎。他分別敗給了《征服情海》的小古巴古汀、《美麗人生》中深受喜愛的羅貝托貝尼尼,以及《進擊的鼓手》中令人不寒而慄的J.K.西蒙斯。除了激烈的競爭,業界也持續有傳聞和報導指出諾頓「難以合作」或尋求對項目高度的創作控制權,例如圍繞他對《美國X檔案》最終剪輯版本的影響力,以及在製作《無敵浩克》期間據報發生的爭議。雖然他的藝術投入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提升了最終成品(如某些人對《美國X檔案》的評價),但這樣的名聲,無論是否完全公平,都可能微妙地影響業界關係,進而影響在一個重視合作的社群中的獲獎前景。
然而,艾德華諾頓的影史地位已然穩固。他自出道以來便被譽為「極具天賦的年輕演員」,因其轉型能力、能無縫切換至陰狠強度的獨特「凡人」特質,以及對角色發展的聰明、往往一絲不苟的態度而備受尊敬。他在《揮灑烈愛》等電影中未掛名的劇本工作,進一步突顯了他更廣泛的藝術貢獻。諾頓的職業生涯始於如此具爆發力、備受好評的角色,使他立即被視為一大才子。雖然他後續的生涯依然強勁且多樣,但奧斯卡獎所需的轉型角色、廣受好評的電影以及有利的競爭環境等因素的特定組合,迄今仍與他無緣。他的藝術張力是他的標誌,但在一個合作與敘事往往在獎項成功中扮演關鍵角色的行業裡,這種張力本身可能成為他奧斯卡之路上的複雜因素。

4. 雷夫范恩斯:細膩與威脅感的掌控大師
雷夫范恩斯被廣泛譽為「來自英國最受歡迎且備受讚譽的演員之一」,他以其「懾人的氣場與張力十足的表演」而著稱。他的職業生涯證明了他「純粹的 versatility(多樣性)」,他能輕鬆駕馭各種角色,從《辛德勒的名單》中的納粹指揮官阿蒙戈特和《哈利波特》系列電影中的邪惡佛地魔等駭人反派,到《布達佩斯大飯店》中迷人古怪的總管古斯塔夫先生,甚至為《樂高蝙蝠俠電影》中的阿福等動畫角色獻聲。
范恩斯在其職業生涯中已獲得三次奧斯卡獎提名(根據提供的資料,第三次為基於2025年初資訊對2025年獎項的預測)。他的首次提名來自《辛德勒的名單》(1993)的最佳男配角。他憑藉《英倫情人》(1996)首次獲得最佳男主角提名,並預計將以其在《樞機主教團》(一部2024年的電影,預計提名2025年奧斯卡獎)中的角色再次獲得最佳男主角提名。
他在史蒂芬史匹柏執導的《辛德勒的名單》中飾演阿蒙戈特,這個令人不寒而慄且難以忘懷的角色為他贏得了國際性的突破,並獲得英國影藝學院電影獎及他的首次奧斯卡提名。史匹柏本人對范恩斯的試鏡印象深刻,他回憶道,他看到了「性方面的邪惡」以及一種能瞬間從「友善時刻」轉為「冰冷無情」的可怕能力。范恩斯曾談及扮演如此黑暗角色的心理負擔,承認在「如此深入地探究那種負面行為」之後,他感到「有點被玷污了」。他所詮釋的戈特被廣泛認為是現代電影中最令人不安的反派之一,一個「有感知力的心態與意識形態的象徵」,其邪惡之所以更加駭人,是因為它植根於歷史現實。
此後,范恩斯憑藉在史詩愛情鉅片《英倫情人》中飾演憂鬱的艾莫西伯爵,獲得第二次奧斯卡提名,這次是最佳男主角。該片在奧斯卡上大獲成功,范恩斯被譽為飾演主角的「完美人選」。雖然他在魏斯安德森執導的《布達佩斯大飯店》(2014)中飾演異想天開的門房總管古斯塔夫H先生並未為他贏得奧斯卡提名,但影評人與觀眾經常將其視為他職業生涯的亮點,一場機智、魅力與無懈可擊喜劇節奏的精湛展現,許多人認為這值得奧斯卡的肯定。近期,他在《樞機主教團》(2024)中飾演紅衣主教湯瑪斯勞倫斯,一個在教宗選舉中以克制和沉靜權威為特徵的角色,為他贏得了影評讚譽和預計的第三次奧斯卡提名。他的表演因其深刻的細膩而備受讚揚,他「讓沉默說話」,並透過「每一個眼神、每一次猶豫的呼吸、每一絲懷疑的閃爍」傳達出巨大的情感深度。
儘管這些演出強而有力且備受讚譽,范恩斯至今仍未贏得奧斯卡獎。在《辛德勒的名單》中,他敗給了《絕命追殺令》的湯米李瓊斯,未能獲得最佳男配角獎。對於這個結果,各方提出了不同的因素,包括瓊斯可能因先前在《誰殺了甘迺迪》中被認為受到冷落而獲得「補償性奧斯卡獎」、業界對瓊斯在塑造《絕命追殺令》劇本及其在片場領導能力上的重大貢獻表示讚賞、范恩斯當時相對而言是個新人,卻飾演了一個極其猙獰的角色,以及范恩斯自己承認他「從未為任何獎項拉票」。至於《英倫情人》,他則在最佳男主角獎項中敗給了《鋼琴師》的傑佛瑞洛許。如今,定義他在《樞機主教團》中備受讚譽演出的那種極致細膩,反而被某些分析家視為在最佳男主角競賽中的潛在劣勢,因為學院往往偏愛「更盛大、更搶眼的表演」。
雷夫范恩斯持久的影史地位建立在他「能融入任何角色,無論是戲劇、喜劇、動作片或動畫片」的卓越能力之上,鞏固了他作為「我們這個時代最優秀演員之一」的聲譽。他早期最具代表性的角色,特別是阿蒙戈特,都相當複雜且往往帶有反派色彩。雖然這些演出備受影評推崇,但奧斯卡有時對於頒獎給飾演極度邪惡角色的演員會有所猶豫,尤其是在他們職業生涯早期,除非該表演和電影取得了壓倒性的文化主導地位(如《沉默的羔羊》中的安東尼霍普金斯)。他後期的作品,以《樞機主教團》為例,展現了對細微之處和內化情感的非凡掌控。這種深刻的細膩雖然是偉大銀幕表演的標誌,但在奧斯卡競賽中,有時可能會被那些更公開轉型或情感更外放的表演所掩蓋。這暗示了一種反覆出現的模式,即范恩斯在他獲提名的角色中所展現的特定才華,並未在那些特定年份或類別中與學院當時的主流偏好完美契合。

5. 山繆傑克森:酷勁十足的王者,仍待一座競爭獎項的桂冠
山繆傑克森是一位電影界的標誌性人物,一位「作品極其豐富的演員,參演超過百部電影」。他懾人的氣場、「深沉權威的嗓音」,以及偏好詮釋「叛逆角色」、「髒話連篇的硬漢角色」和「極具智慧與聰敏的角色」,使他成為同代中最具辨識度且備受喜愛的演員之一。他在1990年代初期嶄露頭角,主要歸功於他與導演史派克李和昆汀塔倫提諾的 प्रभावशाली合作。
儘管他的電影作品豐富且備受讚譽,傑克森僅獲得一次奧斯卡最佳演員獎提名:憑藉在《黑色追緝令》(1994)中令人難忘的角色入圍最佳男配角。2022年,學院以奧斯卡榮譽獎表彰他對電影的巨大貢獻,肯定其終身成就。
為他贏得唯一一次競爭性提名的角色,是昆汀塔倫提諾執導的《黑色追緝令》中的朱爾斯溫菲爾德,這個角色引發了文化現象,將傑克森推向全球巨星的地位。他對這位引用聖經、富有哲思的殺手的詮釋,被認為是電影史上「最引人入勝的反英雄之一」。朱爾斯那段令人振奮的獨白,特別是他對《以西結書》25章17節風格化段落的背誦,立即成為經典,融合了威嚇、靈性以及一段自我發現的旅程。這次演出是傑克森的「突破」,將他轉變為「家喻戶曉的人物」,以及一位備受追捧、適合詮釋充滿活力與張力角色的演員。
他在《黑色追緝令》的最佳男配角獎項中敗給了馬丁蘭道,後者因在提姆波頓執導的《艾德伍德》中轉型飾演貝拉盧戈西而獲獎。傑克森的失望之情溢於言表;當蘭道的名字被宣布時,他被清楚地看到嘴型像是說了「shit」。傑克森對於獎項的看法一直很坦率,他明確表示「獲獎是一種榮譽」,而不僅僅是獲得提名,並且他認為提名往往會被大眾遺忘。他也曾思索,如果《殺戮時刻》(1996)中一段被刪除的場景被保留在最終剪輯版本中,或許能為他贏得一座奧斯卡獎。
山繆傑克森持久的影史地位無可否認。他是現代電影界的標誌性人物,因在眾多賣座強片與備受好評的電影中塑造了無數令人難忘的角色而備受讚譽,其中包括他在漫威電影宇宙中長期飾演的尼克福瑞,以及在星際大戰前傳三部曲中飾演的魅使雲度。他的電影在全球票房總收入已達數十億美元。這樣一位多產且具有文化重要性的演員僅有一次奧斯卡最佳演員獎提名,這本身就相當令人驚訝。他在《黑色追緝令》中敗給馬丁蘭道——一位備受尊敬的資深演員,呈現了非凡的傳記性轉型——可能反映了奧斯卡偶爾對此類角色的偏好,尤其是在與一部來自更非傳統、跨類型電影的角色競爭時。最終授予傑克森奧斯卡榮譽獎,可以被解讀為學院對他對電影藝術巨大且持久貢獻的肯定,或許也算是一種對許多人認為本應屬於他的競爭性獎項的認可形式。

6. 雪歌妮薇佛:科幻女王與戲劇巨擘
雪歌妮薇佛在好萊塢開創了一條獨特且具影響力的道路,她以「在賣座強片中開創性的動作女英雄形象」以及在獨立電影中引人入勝的作品而聞名。她在《異形》系列中飾演的艾倫雷普利不僅是經典;更被廣泛「視為電影史上重要的女性主角」,從根本上改變了女性在動作片與科幻片領域的版圖。
薇佛的才華已獲得三次奧斯卡獎提名。她憑藉在《異形2》(1986)中開創性的角色獲得最佳女主角提名。更令人矚目的是,她在1988年同一年獲得兩項表演獎提名:以《迷霧森林十八年》入圍最佳女主角,並以《上班女郎》入圍最佳女配角。
她在詹姆斯卡麥隆執導的《異形2》(1986)中飾演艾倫雷普利,這是一個分水嶺般的時刻,為她贏得了首次奧斯卡提名,並標誌著「女演員因科幻/恐怖片而獲提名的一大里程碑」,這類電影在過去的奧斯卡主要表演獎項中一直被忽視。影評人一致讚揚她的演出。《洛杉磯時報》的希拉班森將薇佛形容為電影的「熾熱核心」,《異形2》正是圍繞著她「反抗的智慧」與「性感的運動能力」而建構。羅傑伊伯特認為是她堅強、富有同情心的詮釋撐起了整部電影,而傑史考特則宣稱薇佛讓席維斯史特龍和阿諾史瓦辛格等當代男性動作巨星相形見絀,如同「男性海報模特兒」。《異形2》的奧斯卡「遺珠」至今仍讓許多人耿耿於懷,有些人甚至認為這「在37年後更令人扼腕」。在《迷霧森林十八年》(1988)中,薇佛令人信服地詮釋了熱情且具爭議性的靈長類動物學家黛安佛西,為她贏得了最佳女主角提名和一座金球獎。影評人讚揚她的表現,《華盛頓郵報》的哈爾辛森宣稱:「終於,薇佛可能找到了一個與她實力相稱的角色」,儘管有些人認為銀幕上的角色刻劃未能完全展現真實佛西的深度。伊伯特則認為「無法想像有比她更適合這個角色的人選」。
儘管獲得這些強而有力的提名,薇佛至今仍未贏得奧斯卡獎。在《異形2》中,她敗給了《悲憐上帝的女兒》的瑪麗麥特琳。這個結果可能反映了奧斯卡在主要表演獎項上對科幻片和恐怖片的歷史性偏見。1988年,她同時獲得兩項提名,卻在最佳女主角獎項(憑《迷霧森林十八年》)中敗給了《控訴》的茱蒂佛斯特,並在最佳女配角獎項(憑《上班女郎》)中敗給了《意外的旅客》的吉娜戴維斯。同一年獲得兩項表演獎提名,是對演員在該特定電影時期 versatility(多樣性)與影響力的非凡肯定。然而,同時在兩個類別中獲獎極其罕見,而且她在這兩項提名中都面臨了強勁的競爭對手。
雪歌妮薇佛作為女性動作英雄先驅的地位不可磨滅。她的職業生涯展現了非凡的 versatility(多樣性),從《異形》和《阿凡達》等科幻大片中的經典角色,到《魔鬼剋星》等喜劇以及《冰風暴》等備受讚譽的劇情片中的令人難忘的演出。她憑藉《異形2》獲得提名所具有的開創性意義不容小覷;它挑戰了奧斯卡傳統的類型偏好。她未能憑藉那個經典角色獲獎,很可能說明了當時普遍存在的偏見。雖然她在1988年的雙料提名是一項重要的榮譽,但當年兩個獎項的激烈競爭證明是難以逾越的。儘管如此,薇佛對電影的影響,特別是在重新定義女性主角的可能性方面,依然深遠而持久。

7. 威廉達佛:無畏的藝術電影標竿與主流反派
威廉達佛是一位戲路寬廣、張力十足的演員,以其「在主流與藝術電影中飾演多樣角色的豐富職業生涯」而備受讚譽。作為實驗劇團 The Wooster Group 的創始成員之一,達佛為他的表演帶來了一種獨特、往往前衛的感受力。他的作品集證明了他無畏的藝術選擇,以及他駕馭道德光譜上各種角色的能力。
達佛曾四度獲得奧斯卡獎提名,其轉型且引人入勝的演出持續受到肯定。他的提名包括:憑藉《前進高棉》(1986)、《吸血鬼魅影》(2000)及《歡迎光臨奇幻城堡》(2017)入圍最佳男配角;並以《梵谷:在永恆之門》(2018)入圍最佳男主角。
他在奧利佛史東執導的越戰史詩片《前進高棉》(1986)中飾演富有同情心且道德高尚的伊萊亞斯葛洛汀中士,這個突破性的角色為他贏得了首次奧斯卡提名與廣泛好評。伊萊亞斯的角色,特別是他經典的死亡場景,至今仍深植於電影記憶中。伊萊亞斯常被分析為「道德完整性」的象徵,在某些詮釋中,更是在戰爭電影極度陽剛的背景下,體現了感性、情感與關懷等「女性化」特質。在《吸血鬼魅影》(2000)中,達佛飾演麥克斯施瑞克,一位扮演奧洛克伯爵的演員,而這位演員本身可能就是個真正的吸血鬼。他令人著迷且備受好評的演出為他贏得了第二次奧斯卡提名。羅傑伊伯特評論道,達佛「如此逼真地體現了《諾斯費拉圖》中的施瑞克,以至於當那部默片經典的真實片段穿插進畫面時,我們絲毫察覺不到差異」。
他在西恩貝克執導的《歡迎光臨奇幻城堡》(2017)中飾演善良卻疲憊的汽車旅館經理巴比希克斯,這個配角角色廣受讚譽,並為他帶來第三次奧斯卡提名,許多人認為這是他「最接近獲獎」的一次。達佛飾演的巴比在一個充滿絕望的世界中扮演著「唯一穩定且理智的影響力」,充滿了「悶燒的善意」。隨後,他憑藉在朱利安許納貝執導的《梵谷:在永恆之門》(2018)中深刻詮釋文森梵谷而獲得最佳男主角提名。《洛杉磯時報》的肯尼斯杜蘭寫道,達佛的演出「感覺超越了傳統表演,運用直覺和技巧深入角色內心」。Yahoo娛樂將其描述為「朱利安許納貝印象派傑作中一位充滿靈感的梵谷」,這個表演讓達佛本已相當可觀的作品集感覺「更加完整且不可或缺」。
儘管這些演出強而有力且多樣紛呈並獲得提名,達佛至今仍未贏得奧斯卡獎。他分別敗給了米高肯恩(《漢娜姊妹》)、班尼西歐岱托羅(《天人交戰》)、山姆洛克威爾(《意外》)以及雷米馬利克(《波希米亞狂想曲》)。達佛經常選擇在獨立電影和藝術電影中飾演大膽、非傳統的角色。雖然這些選擇往往為他帶來影評讚譽並展現了他令人難以置信的戲路,但它們未必總能符合主流奧斯卡的口味,或者在特定年份可能面臨來自更傳統「奧斯卡誘餌」型表演的激烈競爭。一位Reddit評論員甚至表示,達佛不「玩」奧斯卡政治遊戲,而這有時可能是影響獎項結果的一個因素。
威廉達佛的影史地位是家喻戶曉的,他的職業生涯充滿了「值得獲獎卻從未獲得奧斯卡正式肯定(以獲獎形式)的演出」。他非凡的戲路體現在他能夠詮釋截然不同的人物,例如馬丁史柯西斯執導的《基督的最後誘惑》中的耶穌,以及山姆雷米執導的《蜘蛛人》中瘋狂的綠惡魔。2020年,《紐約時報》將他評為21世紀最偉大的25位演員之一,足證其持久的影響力。達佛的職業生涯是強烈的藝術電影探索與令人難忘的主流角色塑造的迷人結合。他的奧斯卡提名反映了這種兼容並蓄的路線。他的落敗往往發生在他與那些飾演奧斯卡經常偏愛的更傳統戲劇角色或傳記片角色的演員競爭時,或是對手演員正經歷一個重要的「奧斯卡時刻」。他對具挑戰性、有時令人不安的角色的堅定投入無疑是他的藝術優勢,但這種投入本身也可能使他成為奧斯卡獎更複雜的候選人,因為獲獎往往需要更廣泛的共識吸引力或在頒獎季中一個特別強烈的「敘事」。

8. 安妮特班寧:持續發光發熱的傑出女主角
安妮特班寧的職業生涯橫跨四十餘載,以其「在銀幕與舞台上的多樣化演出」而著稱。她的電影成就建立在「卓越的表演實力與對技藝堅定不移的投入」之上,持續呈現細膩入微、能與觀眾產生深刻共鳴的表演。班寧在劇場磨練演技,這份基礎在她可信的詮釋中顯而易見,並成功地轉戰電影界。
班寧曾五度獲得奧斯卡獎提名卻未能獲獎,這證明了她持續的卓越表現以及學院對其才華的穩定肯定。她的提名包括一次最佳女配角提名,來自《千網危情》(1990);以及四次最佳女主角提名:分別來自《美國心玫瑰情》(1999)、《縱情天后》(2004)、《性福拉警報》(2010),以及最近的《泳不放棄》(2023)。
她在史蒂芬佛瑞爾執導的新黑色電影《千網危情》(1990)中飾演誘人的女騙徒麥拉蘭特里,這個突破性的電影角色為班寧贏得了首次奧斯卡提名與廣泛的影評關注。羅傑伊伯特注意到她迷人的「性感、危險與脆弱的結合」,令人想起葛洛莉亞葛拉罕等經典黑色電影女星。雖然當時她或許不像同片演員安潔莉卡休斯頓和約翰庫薩克那樣經驗豐富,但她展現了「 burgeoning talent( burgeoning talent)」,並為一個可能流於膚淺的角色注入了相當的深度。她在山姆曼德斯執導的處女作《美國心玫瑰情》(1999)中飾演物質主義且逐漸崩潰的卡洛琳伯翰,為她贏得了英國影藝學院電影獎、美國演員工會獎以及她的首次奧斯卡最佳女主角提名。影評人讚揚她融合喜劇與戲劇的能力,塑造了一個儘管有缺陷卻能引發同情的角色;她是「與凱文史貝西角色完美對立的人物」。
班寧憑藉在《縱情天后》(2004)中飾演活潑的舞台天后茱莉亞蘭伯特而贏得一座金球獎。《紐約時報》的A.O.史考特讚揚她「敏捷、奔放的魅力」與「令人暈眩、不顧一切的熱情」,而羅傑伊伯特則承認她以「極大的熱情與活力」飾演茱莉亞,即使電影本身是「沉悶的通俗劇」。另一座金球獎則來自她在《性福拉警報》(2010)中飾演的妮可,一位在複雜家庭關係中掙扎的女同志母親。該片廣受好評,班寧的演出尤其獲得普遍讚揚。她最近一次憑藉在《泳不放棄》(2023)中飾演意志堅定的長泳選手黛安娜奈德而獲得提名,部分評論形容其演出「令人印象深刻,即使有些刻板」,但也有人認為電影本身乏善可陳,班寧的表演在未描繪游泳的體能需求時則「表現平平」。
班寧的奧斯卡之路屢屢敗給琥碧戈柏(《第六感生死戀》)、希拉蕊史旺(兩次,分別憑《男孩別哭》和《登峰造擊》)、娜塔莉波曼(《黑天鵝》)以及艾瑪史東(《可憐的東西》)。關於她「早該」獲得奧斯卡獎的說法,尤其在她兩次敗給希拉蕊史旺之後甚囂塵上。然而,部分分析指出,她在《縱情天后》中的演出,例如,只能算是「勉強合格」,能獲得提名已屬幸運,尤其與史旺在《登峰造擊》中強而有力的演出相比。有人認為,雖然班寧的表演一向出色,但有時缺乏奧斯卡得獎角色的決定性「關鍵因素」,或者面臨了對手演員更具代表性、轉型性的演出(例如《第六感生死戀》中的戈柏,或史旺首次獲獎的《男孩別哭》)。
安妮特班寧持久的影史地位是一位備受尊敬的女演員,以其持續在情感層面與觀眾建立連結的能力、她的細膩以及她的坦誠智慧而聞名。她維持著相對私密的生活,將技藝置於名流光環之上。她的職業生涯以持續獲得影評讚譽和因詮釋複雜女性角色而獲得提名為標誌。她的落敗,尤其是兩次敗給希拉蕊史旺,助長了「早該得獎」的說法。然而,仔細觀察可以發現,在那些特定的年份,史旺極具轉型性且對體能要求極高的角色,產生了更顯著的「奧斯卡時刻」影響力。班寧的強項在於細膩、往往內心複雜的詮釋,這些詮釋雖然深受影評人與同行的讚賞(從她眾多的提名可見一斑),但有時可能會被奧斯卡在最佳女主角獎項中經常獎勵的更公開戲劇化或肢體轉型更明顯的表演所掩蓋。

9. 蜜雪兒威廉絲:沉靜張力的演繹大師
蜜雪兒威廉絲以其深刻的內涵與 versatility(多樣性)脫穎而出,因其在電影和電視中引人入勝的角色以及經常選擇「挑戰社會規範的題材」而聞名。她從熱門青少年影集《戀愛時代》轉型成為一位持續備受好評的電影演員,這段歷程證明了她的奉獻精神與不斷進化的才華。
威廉絲已獲得五次奧斯卡獎提名,展現了她非凡的戲路:憑藉《斷背山》(2005)和《海邊的曼徹斯特》(2016)入圍最佳女配角;並以《藍色情人節》(2010)、《夢露與我的浪漫週記》(2011)以及《法貝爾曼》(2022)入圍最佳女主角。
她在李安執導的開創性電影《斷背山》(2005)中飾演默默承受痛苦的妻子艾爾瑪比爾斯戴爾瑪,這個角色為威廉絲贏得了首次奧斯卡提名與廣泛的影評肯定。她的表演被認為比安海瑟薇(飾演另一位主角的妻子)「顯著更強」,艾爾瑪努力面對丈夫隱藏愛情的毀滅性真相。威廉絲本人至今仍對《斷背山》在最佳影片獎項中具爭議性地敗給《衝擊效應》感到困惑,許多人也認為這是奧斯卡的一大不公。在《藍色情人節》(2010)中,威廉絲因其在一段瓦解婚姻中對辛蒂原始且情感豐富的詮釋而獲得最佳女主角提名。她被形容為一位「原始、通透的演員」,她在片中的情感即使在臉部靜止時也顯得「翻天覆地」。她與同片演員雷恩葛斯林因在銀幕上展現「赤裸的情感」而備受讚揚。
她在《夢露與我的浪漫週記》(2011)中轉型飾演瑪麗蓮夢露,為她贏得一座金球獎和另一次奧斯卡最佳女主角提名。影評人認為她的表演「相當出色」,一位評論家表示威廉絲「在外貌和舉止上都如此令人信服地扮演瑪麗蓮,以至於我沒意識到我正在看蜜雪兒威廉絲」。她再次憑藉在《海邊的曼徹斯特》(2016)中飾演蘭蒂錢德勒這個短暫卻強而有力的角色而獲得最佳女配角提名。儘管她的出場時間有限,但她的表演被形容為「值得珍藏的寶藏」,其中與凱西艾佛列克的一場關鍵對峙戲被認為獨具「奧斯卡水準」。最近,她憑藉在《法貝爾曼》(2022)中飾演米茲法貝爾曼——一個以史蒂芬史匹柏母親為原型的角色——而獲得最佳女主角提名。雖然部分影評人認為她的表演「過於誇張」,但也有人認為她準確地捕捉了真實莉亞艾德勒獨特的古怪特質,艾德勒本人的檔案影片也證明了這一點。
威廉絲的奧斯卡之路屢屢敗給瑞秋懷茲(《疑雲殺機》)、娜塔莉波曼(《黑天鵝》)、梅莉史翠普(《鐵娘子》)、薇拉戴維絲(《藩籬》)以及楊紫瓊(《媽的多重宇宙》)。這些都是在各自年份中備受讚譽、往往具有壓倒性優勢的演出。威廉絲經常在需要深刻情感深度與細膩度的角色中表現出色,往往詮釋與悲傷、複雜關係或強烈內心掙扎搏鬥的人物。雖然她憑藉這些強而有力且細膩的演出持續獲得提名,但她經常面對的得獎者往往是那些擁有高度曝光、轉型性角色,或是參與「橫掃千軍」的最佳影片大熱門的演員。她如同在詮釋瑪麗蓮夢露時那樣,能夠完全融入角色的非凡能力,是她才華的標誌。然而,正是那種使她的表演備受好評的細膩與沉靜張力,可能使其在有時偏愛更外放、更「戲劇化」表演的奧斯卡競爭中,顯得不夠「響亮」或不夠公開「戲劇化」。
蜜雪兒威廉絲的影史地位是同代最受尊敬的女演員之一,因其才華、奉獻精神以及為每個角色帶來的深刻內涵而備受欽佩。她對社會正義和性別平等的倡導,進一步提升了她在銀幕之外的影響力。她因需要如此細膩情感演繹的角色而持續獲得奧斯卡肯定,這充分說明了她的技藝,即使最終獎項在強勁的競爭下仍與她無緣。

10. 伊恩麥克連爵士:縱橫舞台與銀幕的戲劇騎士
伊恩麥克連爵士被「廣泛認為是他這一代最偉大的舞台與銀幕演員之一」,這位 versatile(多才多藝)的表演者以其對從莎士比亞經典到當代人物等各種角色的精湛掌握而備受讚譽。作為具影響力的演員公司(Actors’ Company)的共同創辦人及著名的同志平權運動家,麥克連於1991年因其對表演藝術的貢獻而被封為爵士。他的職業生涯是其在戲劇與電影領域奉獻精神的崇高證明。
麥克連曾獲得兩次奧斯卡獎提名:憑藉在《眾神與野獸》(1998)中飾演電影導演詹姆斯惠爾入圍最佳男主角,並以其在《魔戒首部曲:魔戒現身》(2001)中飾演的經典角色甘道夫入圍最佳男配角。
他在《眾神與野獸》(1998)中飾演年邁、備受困擾的電影導演詹姆斯惠爾,為他贏得了首次奧斯卡提名和金球獎提名。影評人對他的演出讚譽有加,詹姆斯貝拉迪內利表示,麥克連「再次證明了為何許多人認為他是同代最優秀的莎劇演員」,他以「力量與不確定性的強大結合」將惠爾演繹得栩栩如生。該片本身被形容為一部「關於慾望、衰老與創造的極其優雅的電影」,以虛構的方式,深刻描繪了惠爾的晚年時光,探索了一段不太可能的友誼以及揮之不去的過往陰影。麥克連的第二次提名來自他在彼得傑克森執導的史詩鉅作《魔戒首部曲:魔戒現身》(2001)中全球知名的巫師甘道夫一角。他的表演被譽為「簡直如同梅林再現」,並因其極具說服力地體現了巫師形象而備受讚揚,賦予甘道夫一種「祖父般溫暖的氣質,卻又能完美轉換為令人敬畏的力量」。
儘管這些演出備受讚譽,伊恩爵士至今仍未贏得奧斯卡獎。他在《眾神與野獸》的最佳男主角獎項中敗給了《美麗人生》中情感濃烈且廣受喜愛的羅貝托貝尼尼。至於《魔戒》,他則在最佳男配角獎項中敗給了《長路將盡》中演出感人的吉姆布洛班特。在這兩次競爭中,對手都異常強勁。貝尼尼的獲獎是《美麗人生》這部擄獲全球情感的電影在國際上取得重大成功的一部分。吉姆布洛班特則是一位備受尊敬的資深演員,在一部傳統劇情片中呈現了動人的演出。
伊恩麥克連爵士的影史地位極其崇高,他在戲劇界的傳奇地位(曾獲多座奧利佛獎與東尼獎)以及在主要電影系列中的經典角色,最著名的莫過於《魔戒》中的甘道夫和《X戰警》系列電影中的萬磁王,都鞏固了他的不朽聲名。他透過這些角色對流行文化的貢獻巨大且不可否認。麥克連的奧斯卡提名來自那些出色展現其古典訓練背景及深刻詮釋複雜歷史與文學人物能力的角色。他的落敗對手,往往是那些呈現了極具情感張力或傳統戲劇性演出,並在當年強烈觸動奧斯卡評審的演員。此外,奧斯卡歷史上也存在一種傾向,即有時會忽視奇幻電影在主要表演獎項中的表現,儘管這些電影在整體評價和商業上都取得了成功,除非該表演具有壓倒性的主導地位或在頒獎季中帶有特別引人注目的敘事。然而,麥克連持久的影響力超越了任何單一獎項。
為何金獎總是與某些巨星擦肩而過
贏得奧斯卡獎的過程,往往比單純呈現一場精彩表演更為複雜。一些潛在的暗流與行業動態,可能影響著為何某些最具天賦的演員屢獲提名卻最終無緣桂冠。
「敘事」因素與公關操作: 奧斯卡獎並非在真空中決定;它們受到整個頒獎季中形成的各種「敘事」所影響。諸如某位演員「早該得獎」、一個「東山再起的故事」,甚至是為了彌補過去被認為受到冷落而頒發的「補償性奧斯卡獎」等因素,都可能在左右選票方面扮演重要角色。製片廠與個人的積極公關也是一個關鍵要素。有些演員,例如雷夫范恩斯,就曾公開承認不參與積極的拉票活動。相反地,山繆傑克森則坦率地表達了他認為榮譽在於獲獎,而不僅僅是獲得提名,這反映了他對獎項競爭本質的理解。因此,奧斯卡獎不僅僅是對銀幕才華的評判,也反映了某個表演和演員如何有效地被「推銷」給學院。一個引人注目的「奧斯卡故事」,有時能讓一位提名者在眾多競爭者中脫穎而出,無論其展現的原始才華如何。
強勁的競爭對手與「時運不濟」: 或許,許多「差一點」得獎最直接的原因,便是特定年份競爭對手的實力過於強大。名單上的許多演員都曾與經典的、一代僅見的表演同場競技,或者在表演獎項競爭異常激烈的年份遭遇眾多傑出作品。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彼得奧圖在《阿拉伯的勞倫斯》中的精湛演出,敗給了葛雷哥萊畢克在《梅岡城故事》中深受喜愛的艾蒂科斯芬奇一角——畢克第五次也是最後一次提名並最終獲獎。例如,葛倫克蘿絲和艾美亞當斯就持續面臨那些繳出重量級表演或受益於強大電影敘事的得獎者。因此,奧斯卡獎的獲得高度取決於特定年份的具體競爭格局;一個在競爭較不激烈的領域可能勝出的表演,當多位傑出競爭者同時出現時,很容易就會黯然失色。
類型偏見與學院偏好: 奧斯卡在表演獎項方面歷來展現出某些偏好。戲劇類角色傳統上比喜劇、科幻、恐怖或動作片中的表演更受青睞。雪歌妮薇佛憑藉科幻動作片《異形2》獲得最佳女主角提名是一項里程碑式的成就,挑戰了這些常規,但並未最終獲獎。比爾莫瑞憑藉融合細膩喜劇與戲劇元素的《愛情,不用翻譯》獲得唯一一次提名,也符合這種肯定跨類型作品但未必授予最高獎項的模式。同樣地,強尼戴普的提名往往來自更奇幻或風格化的角色。此外,奧斯卡尤其在最佳男主角獎項中,常對「更盛大、更搶眼的表演」或涉及重大身體轉型的角色有所偏愛。因此,細膩、內化的表演,例如雷夫范恩斯在《樞機主教團》中備受讚譽的演出,便有被更公開戲劇化表演蓋過鋒頭的風險。這表明角色的類型和電影的類型會顯著影響演員的奧斯卡前景,「較不受重視」類型(就表演獎項而言)或細膩表演所獲得的影評讚譽,未必能像傳統「奧斯卡誘餌」劇情片中的轉型角色那樣輕易轉化為奧斯卡獎。
整體成就 vs. 單一表演: 奧斯卡的投票過程有時可能反映出一種願望,即以「終身成就獎」或「職業生涯獎」來表彰一位備受尊敬的資深演員的整個職業生涯,而非嚴格關注該年度的單一提名表演。這可能意味著另一位在該特定年份有著特別出色表演的演員可能會因此落敗。相反地,像名單上許多演員這樣擁有持續強勁且備受讚譽作品集的演員,可能會發現自己屢獲提名,而投票者或許會認為「他們遲早會得獎」。這種緊迫感的消散,使得任何單一表演都更難以脫穎而出,除非它具有壓倒性的說服力,或者完美契合一個引人注目的「終於輪到他們了」的敘事。因此,奧斯卡的決定往往成為獎勵年度「最佳」表演與肯定對電影長久卓越貢獻之間複雜的相互作用。
「難以抉擇」/選票分散: 雖然並非總能明確證明個別案例,但奧斯卡的投票機制可能導致出乎意料的結果,尤其是在競爭激烈的年份。在充滿多個深受喜愛表演的獎項類別中,選票可能會變得分散。在偏好排序投票制(用於最佳影片)或相對多數投票制(用於表演獎項)中,獲得強大、集中支持基礎的表演可能會勝過其他幾個瓜分剩餘選票的優秀表演。這是一個更具推測性的因素,但在奧斯卡競賽中卻是一個已知的動態,即眾多傑出才華的激烈競爭有時會導致令人驚訝的結果。
小金人之外的榮光
奧斯卡獎的魅力在好萊塢依然強大,它是同行肯定與電影卓越成就的象徵。然而,正如這十位非凡演員——以及許多其他像他們一樣的人——的職業生涯所證明的那樣,未能獲得這座特別的金色小雕像,絲毫無損他們對電影藝術的深遠影響。他們的電影作品充滿了「模範佳作」、經典角色以及不僅獲得影評讚譽和多次奧斯卡提名,更在全球觀眾心中產生深刻共鳴,並以不可磨滅的方式塑造了電影史的表演。
雖然奧斯卡獎無疑能提升演員的職業生涯,並提供一個業界終極肯定的時刻,但衡量這些演員貢獻的真正標準,在於他們表演的持久力量。葛倫克蘿絲令人不寒而慄的張力、艾美亞當斯魅力百變的風采、艾德華諾頓如變色龍般的深度、雷夫范恩斯細膩入微的威脅感、山繆傑克森無可否認的酷勁、雪歌妮薇佛開創性的力量、威廉達佛無畏的藝術性、安妮特班寧持續的精湛、蜜雪兒威廉絲沉靜的張力,以及伊恩麥克連爵士的戲劇莊重——這些特質豐富了電影藝術,遠遠超出了任何單一頒獎典禮的範疇。
他們的影史地位已然穩固,建立在卓越才華、對技藝的奉獻,以及一系列持續啟發並吸引觀眾的令人難忘的角色之上。奧斯卡獎或許至今仍與他們無緣,但他們對電影世界的非凡貢獻無可否認,也必將經得起時間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