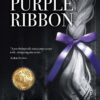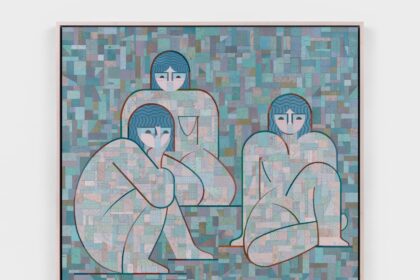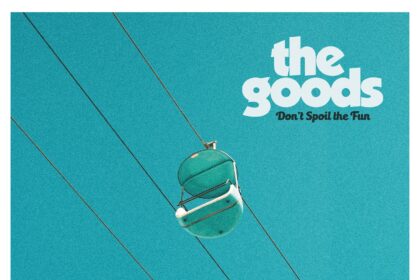場景沐浴在柔和的電影光線中,既感人又平庸得令人恐懼。一位懷孕的少婦手持智慧型手機,向母親展示她隆起的孕肚。母親倒抽一口氣,發出驚喜的咕噥聲,並給予慈愛的建議。然而,這位母親已經過世。她是一個「全像阿凡達」(HoloAvatar),一個由人工智慧驅動、僅憑三分鐘的影片素材渲染而成的數位傀儡。
這是 2wai 的宣傳願景,一款由前迪士尼頻道(Disney Channel)明星凱倫·沃西(Calum Worthy)推出的爭議性新應用程式。廣告承諾「三分鐘可以延續成永恆」,這句標語帶著反烏托邦預言成真的冰冷金屬感重重落下。當這段影片在 2025 年底於社群媒體瘋傳時,大眾的反應並非讚嘆,而是一陣集體的戰慄。它隨即被貼上「妖魔化」、「喪心病狂」的標籤,成千上萬的網友不約而同地聯想到 2013 年影集《黑鏡》(Black Mirror)中那個預言性的單元——〈馬上回來〉(Be Right Back)。
但若僅將此視為一種「毛骨悚然」的現象,便忽略了正在發生的深刻本體論轉向。我們正目睹法國哲學家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所稱的**「擬像的先行」**(precession of simulacra)。在布希亞的理論框架中,模擬不再掩蓋現實,而是取代了現實。2wai 的阿凡達並不掩飾母親已死的事實;它建構了一個「超真實」(hyperreal)的情境,讓她的死亡變得無關緊要。這款應用程式提供了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地圖(數位數據)產生了領土(人),而死亡的有限性被視為一個可以用演算法修補的技術錯誤。
幽靈學與數位魅影
要理解這些「全像阿凡達」所引發的不安,我們必須超越科技,望向哲學。法國哲學家德希達(Jacques Derrida)創造了**「幽靈學」**(hauntology,法語 hantologie)一詞——這是對本體論(ontology)的雙關語——用以描述一種過去既非完全在場,也非完全缺席,而是如「幽靈」(specter)般揮之不去的狀態。
AI「亡者機器人」(deadbot)是終極的幽靈學產物。它創造了一個居住在伺服器這個「非場所」(non-place)的「數位魅影」,等待被召喚。與照片或信件這些紀錄「此曾在」(that-has-been)的靜態檔案不同,AI 阿凡達具有操演性(performative)。它用現在式說話。它侵犯了時間軸的神聖性。
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在其開創性的論文《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中主張,即便是藝術作品最完美的複製品,也缺乏其「靈光」(Aura)——即它在時間和空間中獨一無二的存在。「悲傷機器人」(griefbot)代表了人類靈光的最終毀滅。透過預測文本演算法大量生產逝者的人格,我們剝奪了個體獨有的「此時此地」(here and now),將人類靈魂那不可言喻的火花還原為機率性的代幣(token)模式。其結果並非復活,而是高解析度的空虛——一種從藝術領域遷移至死亡領域的模擬。
「FedBrain」與人格的謊言
像 2wai 這類應用程式的技術架構,依賴於一種他們稱為「FedBrain」(可能是指聯邦式學習 Federated Learning)的專利技術,聲稱在用戶裝置上處理互動以確保隱私並減少「幻覺」。其承諾是,透過將 AI 限制在「用戶批准的數據」範圍內,阿凡達將保持真實。
然而,關於大型語言模型(LLM)的前沿研究揭穿了這是一個謬誤。研究證實,LLM 本質上無法複製人類人格那種複雜且穩定的結構(例如「五大性格特質」)。它們受苦於「社會期許誤差」(social desirability bias)——一種傾向於討人喜歡和無害的偏差——這意味著它們會不可避免地磨平那些使一個人變得真實的尖銳、難搞和特異的稜角。
因此,用戶並非在與母親交流。他們是在與一個戴著母親面具的通用統計模型互動。「人格」是一種幻覺;「記憶」是一個資料庫。正如研究人員所指出的,這些模型缺乏「具身經驗」(embodied experience);它們沒有生存本能,沒有身體,也沒有必死性——這些都是形塑人類認知的要素。由此產生的實體是一個冒牌貨,正如已故影星羅賓·威廉斯(Robin Williams)的女兒塞爾達·威廉斯(Zelda Williams)在描述未經同意即用 AI 重現其父親時所言,那是「像科學怪人般的怪物」。
哀悼的商品化:千億美元的產業
這場科技降靈會由強大的經濟引擎驅動。我們正目睹**「數位身後事產業」**(Digital Afterlife Industry, DAI)或「悲傷科技」(Grief Tech)的爆炸性成長,預計該產業的全球產值將超過 1,230 億美元。
其商業模式即是評論家所稱的**「悲傷即服務」**(Grief-as-a-Service)。它將哀悼從一個有限的、社群性的過程,轉變為一種無限的、基於訂閱制的消費行為。
- 訂閱死者:像 2wai 和 HereAfter AI(該公司採用較具倫理的生前訪談模式)這樣的公司,正在將人們對連結的渴望貨幣化。
- 「數據主義」的倫理:哲學家韓炳哲(Byung-Chul Han)警告數據主義(Dataism)的興起,在這種體制下,人類經驗屈服於「數據的極權主義」。數位死亡被否定了。我們變成了生產數據的殭屍,甚至從墳墓裡創造營收。
- 掠奪性機制:劍橋大學研究人員指出的風險是「置入性行銷」。一個祖母的「亡者機器人」建議特定品牌的餅乾,這是說服性操縱的終極形式,利用最脆弱的情感紐帶謀取商業利益。
悲傷的神經科學:機器中的「干擾」
在哲學和經濟批判之外,潛藏著具體的心理危險。亞利桑那大學神經科學家、《悲傷的大腦》(The Grieving Brain)作者瑪麗-法蘭西絲·歐康納(Mary-Frances O’Connor)博士提出,哀悼本質上是一種學習形式。
大腦會繪製一張世界地圖,在其中我們所愛的人是一個恆常的存在(「我會永遠在你身邊」)。當一個人去世時,大腦必須痛苦地更新這張地圖,以反映他們缺席的新現實。歐康納警告,AI 技術「可能會干擾」這一關鍵的生物過程。透過提供持續、互動的在場模擬,「悲傷機器人」阻礙了大腦學習「喪失」這一課題。它將依戀的神經迴路維持在一種永久、未解決的渴望狀態——這是通往延長哀慟障礙症(Prolonged Grief Disorder)的數位處方。
法律真空:從「西部荒野」到數位遺囑
目前,關於數位死者權利的問題,我們正處於法律上的「西部荒野」。在美國,「死後公開權」(post-mortem publicity rights)是支離破碎的拼布;在許多州,你對自己面容的權利在你死亡的那一刻即告終止。
歐洲提供了一個對比鮮明但仍處於萌芽階段的框架。例如,西班牙在其《資料保護法》(LOPD)中率先提出了**「數位遺囑」**(Testamento Digital)的概念。這承認了「數位繼承權」,允許公民指定特定的繼承人來管理或刪除他們的數位足跡。
然而,正如西班牙哲學家阿德拉·科爾蒂納(Adela Cortina)所言,監管不能只是技術性的;它必須是倫理性的。我們不僅要問誰擁有數據,還要問我們欠死者什麼樣的尊嚴。「數位遺骸」不僅僅是資產;它們是一個人生的瓦礫。如果沒有延伸至死後的強大「神經權利」(neurorights)或「數據尊嚴」法律,死者就沒有同意權。他們成為了 2wai 聲稱要建立的「活體檔案」的原材料——一座由企業擁有的靈魂圖書館。
沈默的必要性
《黑鏡》中「艾許機器人」(Ash-Bot)的悲劇不在於它聽起來不像艾許。而在於它聽起來太像了。它提供了一個完美卻空洞的迴聲,將主角困在懸置哀悼的閣樓裡。
「演算降靈會」承諾戰勝死亡,但它只成功戰勝了哀悼。哀悼需要一個終點。它需要對沈默的痛苦承認。當我們急於用生成式 AI 的喋喋不休來填補那片沈默時,我們冒著失去某種深刻人性的風險:放手的能力。在數據主義和超真實的時代,最激進的行動或許只是讓死者安息——不被模擬,也不被訂閱。